|
雪晶,侯丹,王旻烜,张佳,张家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摘要:生物质能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及唯一的可再生碳源。发展生物质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围绕生物航煤、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主要生物质能利用形式,介绍了国内外产业及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其中,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产业整体稳步发展,产业技术相对成熟,生物航煤起步虽晚但进展快速;未来提高经济可行性、非粮原料和劣质原料适应性、产品的市场适应性是生物质能技术升级方向。结合道达尔、壳牌、埃克森美孚、BP、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等国内外主要能源公司在生物质能领域的实践经验及业务进展,阐述了我国加快发展生物质能的必要性。建议我国大型能源企业发展生物质能产业时应抓住时代机遇,做好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整体布局、整合资源力量,加快实质性建设步伐,以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发展。
生物质能指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生物质能中的碳来自大气中的CO2,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不增加大气中的碳总量,是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形式,也是唯一可替代化石能源转化成液态、固态和气态燃料及其他化工原料或产品的碳资源。生物质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最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鼓励甚至强制推广使用生物质能。我国已将生物质能作为六大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之一。
目前,生物质能已成为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在内众多大型能源公司新能源领域重点发展的业务。本文重点围绕生物液体燃料,对全球主要国家地区生物质能产业和技术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结合国内外主要能源公司在生物质能领域的应用实践,对我国大型能源企业发展生物质能提出建议。
1世界生物质能产业与技术发展
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沼气、生物质发电是生物质能源的主要利用形式。从全球看,生物液体燃料、生物质多联产发电、生物天然气的技术、装备和商业化运作模式已经成熟,产业规模正在快速扩展。生物液体燃料可直接替代石油燃料,又可进一步生产其他化工品,是生物质产业中最具商业应用价值的方向。
1.1产业发展现状
1.1.1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稳步发展
燃料乙醇是世界消费量最大的液体生物燃料。据美国可再生燃料协会统计[1],2019年,世界燃料乙醇产量8672×104t,比2014年增长16%(图1),混配出约6×108t乙醇汽油,超过同期全球车用汽油消费总量的60%。全球有66个国家推广使用乙醇汽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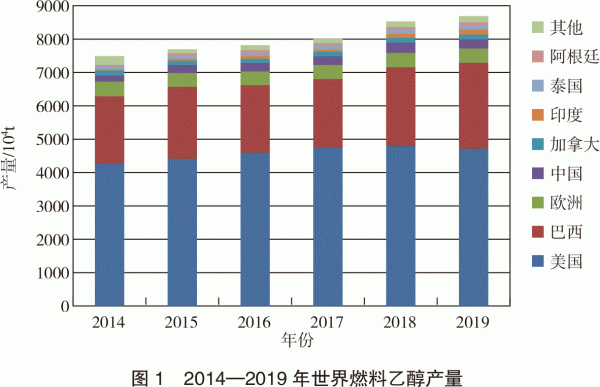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燃料乙醇生产国,2019年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54%,主要以玉米为原料。E10乙醇汽油在美国基本实现全境覆盖,并逐步开始使用E15乙醇汽油,此外E15~E85混配的乙醇汽油也在探索中。巴西是世界第二大乙醇汽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以甘蔗为主要原料,2019年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0%,燃料乙醇替代了巴西国内约一半以上的汽油。
全球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美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西和欧盟[2]。据德国《油世界》历年统计数据,2008年以来,全球生物柴油产量快速上涨(图2),2018年全球生物柴油产量约为4020×104t,2019年已超过4500×104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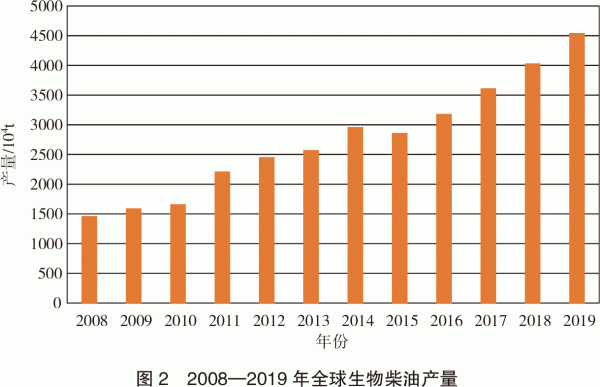
欧盟以菜籽油为主要原料,是世界上生物柴油产量最大的地区,约占成品油市场的5%。德国生物柴油已替代普通柴油使用,产量占可再生能源总量的60%以上。法国是欧盟生物柴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年均增长率近20%。美洲主要以大豆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据EIA数据,截至2019年,美国共有102家生物柴油工厂,总产能约为890×104t/a。巴西正在新建及扩建的生物柴油工厂共21家,建成后产能将增至1100×104t/a。东南亚国家主要以棕榈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印度尼西亚于2020年1月1日启动B30生物柴油计划,年消费量目标为834.34×104t。马来西亚规定从2019年2月起,生物柴油掺混率从7%提升至10%,并计划在2025年前进一步提高至30%。
1.1.2生物航煤快速崛起
目前,全球民航业商业航班的航煤年消费量约为2.7×108t,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约为8.59×108t,占行业排放总量的96%以上。由于航空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平流层,对气候变化影响更大,开发应用可实现碳减排的航空替代燃料已成为国际民航业的普遍共识。国际民航组织(ICAO)已于2019年1月1日实施国际航空全球碳抵消和减排机制,要求以2019—2020年航空碳排放量为基准,在2021—2035年保持零增长。截至2019年,全球采用航空生物燃料的载客商业飞行已超过16万架次,有40多家航空公司使用生物航煤[3]。
美国、加拿大、挪威、芬兰等国已经形成航空生物燃料规模化市场,建立了“原料—炼制—运输—加注+认证”的完整产业链。美国、瑞典、挪威的7个机场已实现生物航煤常规加注,8个机场进行了航空生物燃料的批次加注[4]。
共有5种航煤产品列入ASTMD7566-15c附件且完成燃料试飞。HEFA路线(油脂加氢脱氧—加氢改质)由于生产成本最低,已陆续投产。目前,全球已建成10余套生物航煤生产装置或示范装置,9个项目正在筹建[5]。各大能源公司、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积极参与生物航煤的研发、生产或试用。全球主要的加氢法生物航煤生产装置如表1所示。截至2019年,生物航煤订单量累计已达635×104t。根据CORSIA实施方案,2021—2035年,我国生物航煤需求总量可达(1.6~1.8)×108t。

1.1.3其他生物质能同步发展
生物沼气提纯后甲烷纯度可达97%以上,可用来加热、发电或作为车用燃料。2018年,全球沼气产量约580×108m3,其中德国沼气年产量已超过200×108m3,瑞典生物天然气满足了国内约30%的车用燃气需求[7]。
生物质可直燃或与煤混燃进行发电。直燃电厂单机容量一般为25~30MW,锅炉燃烧效率为80%~90%,发电效率为20%~30%,通过热电联产可节约燃料约28%,减排CO2约47%,能量利用率达80%~90%。混燃电厂单机容量多为50~100MW,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4%,发电效率约为49%。目前全球已有200多座混燃示范电站,其中100多套在欧盟,60多套在美国,其余在澳大利亚等国。美国将生物质发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重要形式,预计2020年将利用生物质发电1880×108kW•h。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体系已基本形成,2017年生物质发电量约为三峡全年发电量的81.4%,占整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4.67%,预计2020年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104kW,年发电量超过900×108kW·h[7]。
1.2产业发展趋势
生物质原料来源极为丰富,但目前利用率仅为2%~3%。尽管成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物质能的发展,未来生物质能将在新能源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IRENA调查问卷显示,生物液体燃料仍是生物质能最具商业价值的方向,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国际协议、经济性是影响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国际协议对SOX、NOX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将促使飞机、轮船等重型运输工具转向使用生物液体燃料。约65%的被调查者认为,未来5~15年,车用燃料电池并不会对生物液体燃料市场构成大的威胁[8]。经济性是产业发展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副产品和联产产物将成为生物燃料具有商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与车用液体燃料相竞争的多种新能源形式相继出现并快速发展,在航运航空等要求能量密度高、难以电气化的行业中,生物液体燃料更具优势[8]。随着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的实施,生物航煤产业将进入快速上升期。美国计划到2025年,生物质燃料替代中东进口原油的75%,2030年生物质燃料替代车用燃料的30%。日本计划将车用燃料中乙醇掺混比例达到50%以上。印度、巴西、欧盟分别制定了“阳光计划”“酒精能源计划”和“生物燃料战略”,加大生物质燃料的应用规模。预计到2035年,生物质燃料将替代世界约一半以上的汽柴油,经济环境效益十分显著[9]。
1.3技术发展现状
1.3.1生物航煤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性有待提升
生物航煤与石油基航煤的组成与结构相似,性能接近,可满足航空器动力性能和安全要求,不需更换发动机和燃油系统,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幅度为67%~94%,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燃料替代方案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途径。生物航煤技术发展迅速,自2009年以来,已有6种技术路线通过ASTMD7566认证(表2),分别是费托合成制备生物航煤(FT-SPK)、油脂加氢脱氧制备生物航煤(HEFAs)、糖发酵加氢制备生物航煤(SIP)、轻芳烃烷基化制备生物航煤(SPK/A)、低碳醇制备生物航煤(ATJ-SPK)[10]、催化水热裂解喷气燃料(CHJ)[11]。这些技术路线的成本均较高,其中HEFAs路线是目前成本较低、应用最广泛的生产技术,以非食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通过两段加氢(前加氢脱氧、后加氢改质)工艺生产生物航煤,产品包括石脑油、生物航煤、生物柴油及重组分燃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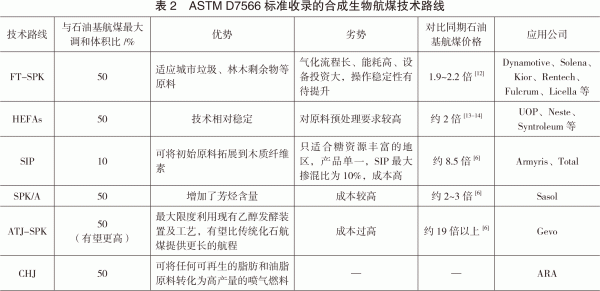
1.3.2燃料乙醇技术逐渐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
以粮食为原料的第一代燃料乙醇技术成熟度高,是目前国内外燃料乙醇商业化生产的主要技术。玉米是第一代技术最常用的原料。为了充分利用玉米颗粒中与纤维相连的淀粉(约占玉米质量的1%~2%),开发了玉米纤维乙醇技术,增加对粉碎调浆后原料再次细粉碎、对发酵前后分离玉米纤维预处理等环节,使乙醇产量最多提高10%,高品质DDGS蛋白质含量提高10%以上[15]。目前,ICM、Syngenta、D3MAX、FQTP和Edeniq这5家公司已将玉米纤维乙醇技术商业化。
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是未来生物燃料乙醇行业的发展方向,但目前商业运行仍面临预处理效率低、纤维素酶成本高等瓶颈,一些示范项目由于经济目标无法达成而停产或出售。仅有美国艾奥瓦州的POET-DSM公司7.5×104t/a玉米芯/玉米秸秆产乙醇示范项目、巴西圣保罗州的Raizen & Iogen公司3.2×104t/a蔗渣乙醇示范项目[7]和我国的龙力公司5×104t/a玉米芯乙醇项目运行良好。
第三代微藻燃料乙醇技术代表着更超前的研究方向。该技术路线具有光合效率高、生产周期短、吸收大气中CO2等显著优势,目前正处于研发起步阶段。涉及的高效光生物反应器、工程藻株开发、有害生物污染控制、低能耗微藻收集、高抗逆性的菌种培育等技术有待突破,还远未达到工业化生产水平。
1.3.3生物柴油技术相对成熟,提高原料适应性是关键
生物柴油制备方法通常分为酶催化法、超临界或近临界法、酸催化法和碱催化法[16-19],整体技术较成熟。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德国Lurgi公司开发的均相碱两级连续醇解工艺,已经承建的生产能力为(10~25)×104t/a生物柴油的生产装置超过40套。碱催化法需要严格限制原料中的游离酸和水含量(通常小于0.5mgKOH/g,几乎无水)[20],具有催化剂廉价、反应条件温和、反应速率较快等优势。法国石油研究院(IFP)开发了Esterfip-H工艺,使用具有尖晶石结构的锌铝复合氧化物固体碱催化剂[21],能显著简化产品后处理。目前利用该技术承建的生物柴油生产装置总生产能力超过80×104t/a。我国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废弃油脂和地沟油,国内民营企业主要采用先将均相酸催化预酯化,降低酸值,然后均相碱催化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
近年来,业界有尝试通过催化加氢工艺得到成分类似于石油基柴油的燃料,由于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的定义,被称为“绿色柴油”或“可再生柴油”。生产绿色柴油的工艺主要分为独立加氢工艺和共加氢工艺。芬兰Neste的NExBTL工艺、美国UOP和ENI公司的Ecofining工艺均是典型的独立加氢工艺,通过对动植物油脂进行加氢脱氧异构生产绿色柴油,也可用来生产生物航煤。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发的H-BIO共加氢工艺,将部分动植物油脂加入柴油精制进料中进行掺炼,既可提高柴油产量质量和产品十六烷值,还可节省投资[22]。与传统生物柴油相比,绿色柴油十六烷值高,低温流动性好,与石油基柴油相容性更好,但收率略低,且投资成本是传统生物柴油的1.5倍[23],目前推广应用有限。
1.3.4生物沼气技术向高值化利用方向发展
欧盟地区沼气技术世界领先,德国、丹麦等国多采用传统全混式沼气发酵工艺,工程技术及装备已达到系列化、工业化水平。其特点是:(1)规模较大,平均池容约为1000m3;(2)产气量高,可达15m3/m3;(3)厌氧反应器能耗较低,发电余热利用率达90%;(4)技术装备标准化。不过,生物沼气替代燃煤直接燃烧经济性较差,沼气发电或提纯后作为生物天然气进入管网或用作车用燃气附加值较高,因此,沼气净化技术是生物沼气高值化利用的关键[24]。目前,我国沼气利用仍以代替原煤直接燃烧为主,只有约1%用于发电,提纯项目更少。
1.4技术发展趋势
世界各国重视生物质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业经济性是生物质科技特别是生物液体燃料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生物航煤技术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原料成本、催化剂成本、产品收率等问题亟待解决。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的第二代技术是未来燃料乙醇产业的发展方向。生物柴油制备技术正朝着提高原料适应性、降低能耗、减少物耗和排放的方向持续改进。高值化利用是生物沼气的发展方向,生物质发电是将农林废弃物和垃圾规模化能源利用的重要途径。
1.4.1经济可行是生物质能技术升级的方向
降低成本是未来生物质能技术攻关的重要目标,也是产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开发高效纤维素预处理工艺、低成本纤维素酶生产、低氢耗油脂加氢脱氧技术、劣质油脂原料深加工高值化利用技术、长寿命催化剂制备技术、藻种基因诱变技术、沼气提纯净化技术、气化发电技术等,都是改善技术经济性的重要研究方向。据预测,到2030年,纤维素乙醇成本将与汽油成本相当,生物沼气成本可低于天然气成本,生物质发电技术成本与燃煤成本持平[24],生物柴油、生物航煤将更具商业竞争力。
1.4.2市场适应性强的联产技术将更受青睐
处于市场经济环境,面对激烈的产业竞争,一方面降低原料成本,另一方面实现产品高值化是生物质能的技术发展趋势。生物乙醇联产功能糖及电力、生物航煤联产生物柴油及化学品、生物质热电联产等,将在工程设计、系统集成中更受重视。
2国外主要能源公司探索与实践
国外多家大型能源公司均较早进入生物质能领域并进行各有侧重的探索,核心皆是以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煤为主的生物液体燃料。
2.1道达尔探索生物质能起步早
1992年,道达尔开始研发第一代生物燃料,由乙醇生产乙基叔丁基醚(ETBE)及植物油甲酯(VOME),并逐步在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拥有(含合作拥有)7套ETBE生产装置,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炼厂在柴油中调入VOME。之后,与Neste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绿色柴油/生物航煤(NExBTL)。2015年,道达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开设以研发发酵工艺和生物分子净化技术为主的生物工艺平台。2019年,公司出资改建的法国第一座生物燃料工厂La Mede投产,70%原料来自植物油,30%来自处理后的废油,产品为绿色柴油和生物航煤[25]。
2.2壳牌致力于推动非粮原料利用
2011年,壳牌与巴西第三大生物燃料公司Raizen合作利用甘蔗生产燃料乙醇,开始大规模生物燃料生产,2016年底产能达20.4×108L/a。同时,壳牌致力于开发应用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技术,在美国休斯敦建造2座纤维素乙醇生产厂,在印度班加罗尔建设1座纤维素乙醇生产厂。目前,纤维素乙醇技术可行,但经济成本偏高,随着技术进步,未来有望实现规模化商业生产。2019年,壳牌与香港美心集团合作,利用食用废油生产生物柴油,并通过3个加油站为香港船队、货运卡车等提供生物柴油[26]。
2.3埃克森美孚关注第三代生物燃料技术
2009年,埃克森美孚与生物基因公司Synthetic Genomics合作,投资6亿美元用于微藻生物燃料研发。2018年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种植天然藻类进行室外实地研究,预计到2025年,每天可以生产1×104bbl藻类生物燃料[27]。2019年,埃克森美孚和可再生能源集团(Renewable Energy Group,REG)与瑞士ClariantAG公司合作,研究利用微生物一步发酵过程,将复杂的纤维素糖转化为低碳生物柴油[28]。
2.4BP生物质能业务核心是燃料乙醇和燃料丁醇
自2008年起,BP先后收购巴西热带生物能源公司Tropical BioEnergia SA、美国生物燃料技术公司Verenium Corp、巴西乙醇生产企业Cerradinho、巴西燃料乙醇生产企业Companhia Nacionalde Acucare Alcoo部分股份或业务。2019年,BP与美国农业商品公司Bunge共同出资在巴西推进生物燃料和生物发电业务,目前已拥有11个生物燃料生产基地,甘蔗乙醇产能为3200×104t/a,成为巴西甘蔗乙醇生物燃料行业第二大参与者[29]。此外,BP还与杜邦公司成立了生物燃料合资公司Butamax,率先开发了插入式生物燃料丁醇汽油,解决了车辆及基础设施与生物燃料兼容性的关键问题。
近年随着欧美国家在生物能源领域政策推动力度的加大,国外大型石油公司纷纷进入生物质能领域。从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到合作建设生产厂,从粮食基原料拓展到非粮纤维素及藻类原料,从尝试性介入到实质性扩大规模,逐渐掀起了传统石油公司开发生物质能的热潮[30]。
3中国加快发展生物质能的战略意义、现状与规划
3.1加快发展生物质能的战略意义
3.1.1发展生物质能契合我国能源转型的现实需求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1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为近50年来最高[31],能源安全形势严峻。与此同时,全球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恶化,各国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能源供应模式。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承诺碳排放于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而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核心。与其他新能源相比,生物质能技术研发起步较早,技术相对成熟,且生物质能的碳源来自自然界,在全生命周期内呈碳中性,能有效改善传统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因此发展生物质能成为这场能源革命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
3.1.2生物质能具有独特的资源及性能优势
化石能源不可再生且资源有限,据BP《2020年世界能源统计报告》发布,2019年底我国石油探明储量为36×108t,占全球储量1.5%,储采比为18.7年。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可利用的农林废弃物、油脂、畜禽养殖和生活垃圾等有机废物供应量超过4×108t/a(折合标准煤),仅餐饮业废油等劣质油脂资源约为1000×104t/a。木质素和纤维素以约2000×108t/a的速度再生,按能量换算,相当于石油产量的15~20倍。未来能源将呈现多元化趋势,生物质能具有其他新能源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更适合转化成液体运输燃料,可与化石能源一样用于塑料和化工原料等下游产品生产。此外,生物液体燃料可作为应急能源提供重要保障,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3.1.3我国在生物质能领域积蓄了大量实践经验
我国是发展生物质能较早的国家,乙醇汽油已推广应用近15年,建立了稳定的原料供应渠道、合理的定价机制。粮食基乙醇适度发展,纤维素乙醇由示范向产业化过渡的趋势逐渐明朗。生物航煤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以小桐子油、蓖麻油、废弃油脂、纤维素等不同原料、不同工艺的技术路线均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技术经济性、转化效率、原料供应渠道、劣质原料与工艺的匹配性等问题,在技术放大的过程中受到更多关注,为工业化成套技术研发和工业示范指明了方向。生物沼气已由小规模户用沼气,向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和生物天然气工程升级,高值化利用导向清晰。配合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动政策,前期实践积累和当前技术突破为现阶段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3.2发展现状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2019年产量约为269×104t[1],产能约为317×104t/a,其中以玉米为原料的乙醇产能占57%,木薯占25%。基于木质纤维素的第二代燃料乙醇技术持续优化,已经进行工业示范,正处于规模化应用的起步阶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有13个省市使用乙醇汽油,包括天津、黑龙江、河南、吉林、辽宁、安徽、广西、山西8省市全境和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湖北5省31地市。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第一代燃料乙醇技术进行生产,主要原料为玉米等淀粉类原料,发酵产乙醇工艺可分为“干法”和“湿法”。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采用“干法”技术,玉米经干燥粉碎后加入水成糊浆,再进行液化、糖化、发酵、蒸馏、脱水;吉林燃料乙醇采用“改良湿法”技术,玉米经湿式粉碎,只分离出玉米胚芽并提取胚芽油,剩余淀粉经液化、糖化等。副产品均为酒糟蛋白饲料DDGS/CO2。
我国生物柴油生产目前普遍采用较成熟的酸碱催化技术,即先通过均相酸催化进行预酯化,降低原料酸值,然后进行均相碱催化酯交换,制取生物柴油。该技术成本较低,但存在工艺流程长、物耗大、废物排放多等问题。2010年,我国拥有生物柴油企业约150家,总产能约为350×104t/a,年产量超过100×104t。2015年,由于税收政策调整、原料供应不足及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等原因,多数企业经营困难,截至2018年,生物柴油生产企业已缩减为40~50家。近3年,我国生物柴油市场逐渐好转,出口量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生物柴油产量103×104t,其中出口30×104t。上海、昆明等地在公交系统开展生物柴油试运行,效果良好,国内生物柴油消费市场正在形成。
我国生物航煤技术发展势头迅猛,2011年以来已完成4次生物航煤飞行试验(表3),目前尚未形成产业,仅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获得生物航煤适航许可证,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10×104t/a生物航空生产装置即将建成。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均采用的是HEFA路线下的两步法加氢脱氧技术,即生物质原料经预处理脱除掉磷、钠、钙、氯等杂质后,通过加氢脱氧得到长链烷烃,再经加氢改质使长链烷烃发生选择性裂化和异构化反应,生成异构烷烃,最终分馏得到生物航煤等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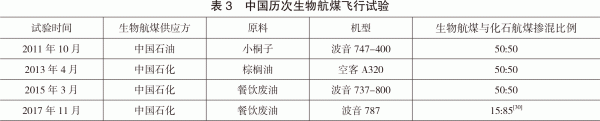
3.3发展规划
据《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路线图2050》[9],我国生物质能的利用总量在2030年、2050年将分别达到2.42×108t标准煤和3.37×108t标准煤。未来,生物液体燃料将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原料增量将基本用于生物液体燃料的生产需求。预计到2050年,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总量约占同时期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5%~8%。
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33]提出,尽快在全国推行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推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2017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指出以生物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生物能源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基本实现全覆盖,生物燃料乙醇使用规模达到1100×104t左右;纤维素燃料乙醇5×104t级装置实现示范运行。
国家能源局2014年11月发布《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政策》[34],提出构建适合以废弃油脂为主、木(草)本非食用油料为辅的可持续原料供应体系,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推广使用生物柴油,鼓励公交、环卫等政府管理的车辆优先使用生物柴油调和燃料。国家《“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要求民航业推进新能源应用等绿色民航项目实施,保障行业分解目标完成。《环境保护税法》对大气污染物(CO、SO2、NOx等)开始征税,进一步扩大了航空公司对生物航煤的需求。据IATA预测,未来5~10年生物航煤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000万美元。预计2021—2035年,我国生物航煤需求总量可达(1.6~1.8)×108t。
4国内两大石油企业生物质能业务进展
中国石油是国内最早进行生物质能研究和应用的公司之一。燃料乙醇方面,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政府批准建立的国内第一个专业化大型燃料乙醇生产基地,现拥有产能60×104t/a,采用国内首创的改良湿法工艺,实现了原料转化率高、装置运行周期长、能耗物耗低、节能效果显著、副产收率高等目标。中国石油还积极开展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技术攻关和第三代微藻燃料乙醇技术探索。生物柴油方面,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简称中国石油石化院)在开发原料适应性强、流程短、产率高的生物柴油制备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有望降低生物柴油生产成本;绿色柴油技术研发在加氢脱氧、异构降凝催化剂和工艺等相关技术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生物航煤方面,2011年10月28日,中国石油牵头成功进行了我国首次生物航煤验证飞行。之后,迅速启动加氢法生物航煤重大科技专项,开展核心催化剂自主开发、工艺包设计、标准方法建立等一系列科技创新工作。为进一步降低成本,中国石油石化院持续研发新一代生物航煤技术,设计开发了新的催化工艺技术,有望显著改善生物航煤的技术经济性。
中国石化在非粮作物生物燃料生产领域开展了积极实践。燃料乙醇方面,2006年,中国石化与中粮合作建设广西合浦20×104t/a木薯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已于2007年12月投产;2009年2月,中国石化与中粮及其合作伙伴诺维信达成协议,共同开发纤维素燃料乙醇;2018年,与江西雨帆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合建10×104t/a木薯燃料乙醇项目。此外,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石化石科院)在产油微藻种库建设、大规模养殖微藻技术、微藻脱硝组合工艺技术等方面积极探索。生物柴油方面,中国石化石科院成功开发出SRCA生物柴油技术,2009年应用于海南6×104t/a生物柴油工业装置,后又开发第二代生物柴油技术(SRCA-II)。生物航煤方面,2011年,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改建生物航煤工业装置及调和设施,同年12月生产出合格生物航煤;2014年2月,获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生物航煤适航许可证,可投入商业化应用[33]。
5我国能源企业加快发展生物质能的建议
5.1抓住时代机遇,扛起国企担当
当前,生物质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大型能源企业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履行节能减排承诺的责任,应加快推进生物质能业务发展,稳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当好国家能源革命的排头兵。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对培育新能源经济增长点、助力能源企业在时代浪潮中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5.2做好顶层设计,优化整体布局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能源转型的时代变革中,绿色环保将是能源行业新的核心竞争力。大型能源企业必须敏锐把握生物质能领域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能源转型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投资布局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配合国家出台的试行试点政策,支撑现有业务发展和产业链升级,为实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5.3整合资源力量,加快实质性建设步伐
生物液体燃料是唯一可替代石油基燃料使用及后加工的碳资源,也是链接能源企业、特别是石油公司主营业务和新能源业务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因此,有必要加快资源整合,形成科技创新体系,从应用基础研究、重点攻关和试验、集成配套推广应用3个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顶层设计,着力关键技术节点“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加快生物质能产业化建设步伐,推动生物质能在能源补充和能源转型中发挥更重要的支撑作用。
5.4加快技术创新,支撑产业发展
生物质能技术的开发,既要解决原料的工艺适应性问题,也要考虑产品的市场适应性问题。一方面应加快开发劣质原料适应性强、主产品收率高的生物质能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开发产品结构拓展性强、过程成本低、副产品价值高的生产工艺,使技术体系更具柔性,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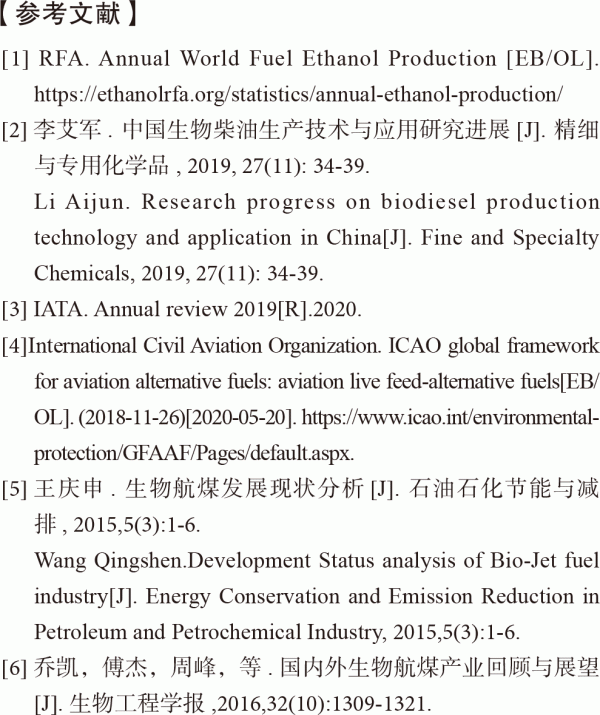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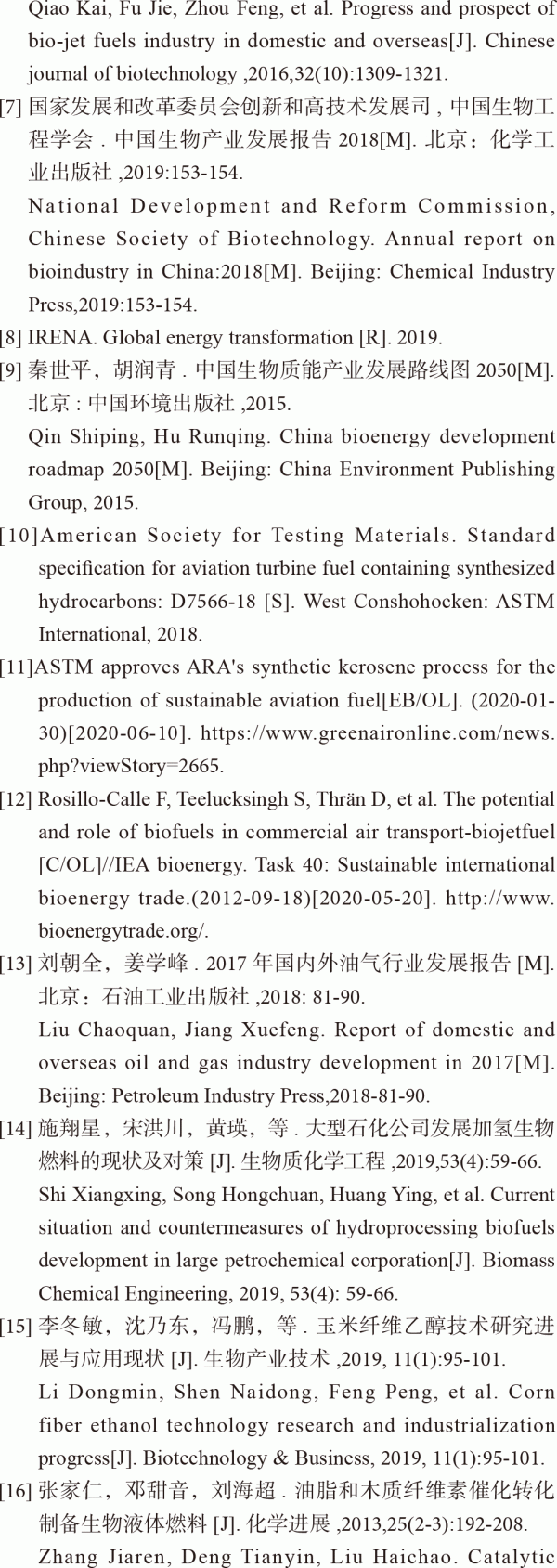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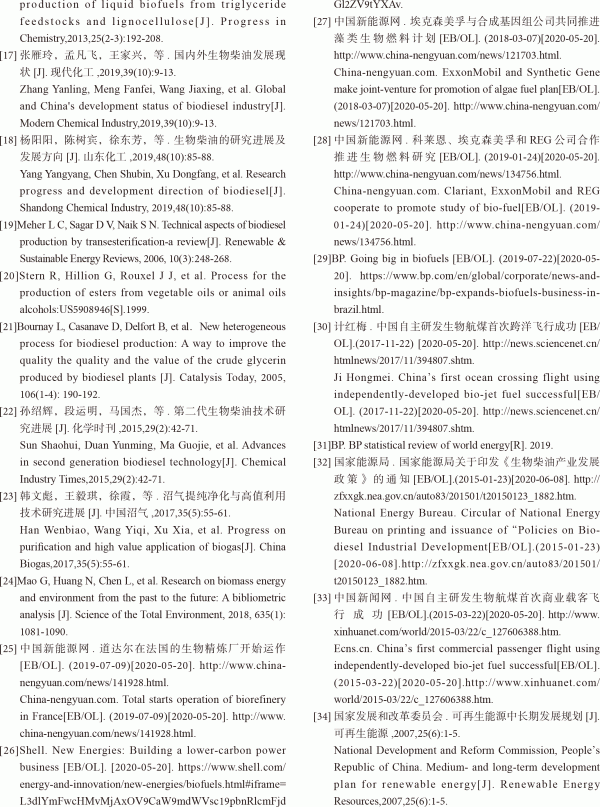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