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祖梁1,3,邵宇航2,王飞1,3,王久臣1,3,孙仁华1,宋成军1,李想1
(1.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北京100125;2.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江苏南京210095;3.农业农村部变源指环利用技术与模式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4)
摘要:[目的]为加快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方法]文章在系统梳理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文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我国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发展阶段,提出了秸秆利用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我国秸秆综合利用从时间序列上,可以划分为起步阶段、强力推进阶段和攻坚阶段。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能源结构的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农作物季节矛盾突出等,成为秸秆综合利用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当前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存在四大方面问:秸秆还田成本较高、区域技术规范和技术适宜性缺乏;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秸秆产业化利用发展闲难;秸秆收储运成本高,技术装备水平低,用地、运输问题尚未解决,收储运体系建设不健全;关键性政策工具尚未破题、缺乏普惠性、针对性的资金扶持。[结论]针对形势与问题,提出了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4条对策建议:开展县械秸秆全量化利用、分区施策确定秸秆利用方向、加强政策工具集成创设、扩大试点示范引导。
0引言
我国农作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小麦、水稻、玉米、豆类、薯类、棉花、花生、油菜、甘蔗以及其他杂粮作物。秸秆是农作物收获籽实后的剩余部分,是宝贵的生物质资源。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产量逐年递增,秸秆产生量也随之增加。至2015年我国秸秆资源总量已超过10亿t,居世界秸秆总产量的20%-30%[1],其中小麦、水稻,玉米3类作物秸秆占总量的80%左右[2]。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约为80%左右,仍有2亿t左右的秸秆通过不同途径进行焚烧或废弃。前人研究表明,秸秆焚烧的总碳排放量相过5000万t[3],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2016年国家发改委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纳入《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的依据;2017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制度,加强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提开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破解秸秆焚烧困境,文章在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秸秆综合利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总结凝炼,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相关建议,以期为秸秆资源化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1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发展阶段
我国重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近20年,从时间序列上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97-2007)。此阶段主要特点是以狠抓禁烧为主。1997年农业部连续两次下发《关于严禁焚烧秸秆,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紧急通知》,从全国层面开始启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1998年农业部、财政部、交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民航总局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的通知》,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推动秸秆禁烧工作;1999年国家环保局、农业部、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下发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开始从法律层面推动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其后环保部每两年发布一次禁烧通知,并将秸秆焚烧火点纳入国家卫星遥感监测范围,推动秸秆禁烧的常态化管理,秸秆露天禁烧现象得到初步遇制。到2007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68.7%。
第二阶段,强力推动阶段(2008-2015)。此阶段主要特点是明确责任分工,强化顶层设计,做好规划引领。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各部门的任务分工,以及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达到80%的目标。依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国家发改委、农业部指导各省(市、区)编制秸秆综合利用规划、制定实施方案、印发技术目录,强势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初步形成了肥料化、饲料化等农业利用为主,能源化、原料化、基料化多元发展的格局。到2015年底,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1%[2]。
第三阶段,攻坚阶段(2016一)。此阶段主要特点是财政投入、试点示范、以点带面,整县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十二五”末,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环保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提出至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的目标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通过修订,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晰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方面的内容。2016年,农业部、财政部以县为单元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建设,围绕重点区域、关键环节、模式探索、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大攻关力度,逐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水平。2017年,农业部启动了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动,聚焦东北秸秆处理利用的重点难点,开展集中攻关。同时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不断完善秸秆资源化利用制度,切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2秸秆综合利用面临形势
2.1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20余年[4],城镇化率从1990的26.41%提高到2017年的57.35%。伴随着城值化的推进,乡村人口数量大幅减少,从1990的8.41亿降至2017年的5.77亿[5],年均降幅1.2%,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经商,老人和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6],造成秸秆还田、离田利用困难逐断加大,焚烧废弃现象屡禁不止。
2.2农村生活能源结构调整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秸秆为主要燃料的农村传统能源利用方式逐渐被电、煤、天然气、太阳能等商品能源和新型能源所取代。研究表明,我国农村生活能源总消耗量从1991年的58亿t标煤逐渐升高至2011年5.89亿t标煤,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6年为3.52亿t标煤,基本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持平。而生活能源中秸秆的消耗量则从1991年的1.62亿t标煤下降至2016年的0.41亿1标煤,降幅达到74.69%,其在农村生活能源中所占比重也从45.31%减少至11.67%[7-8]。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调整,秸秆需求量的下降要求秸秆综合利用寻找新的出口和方向(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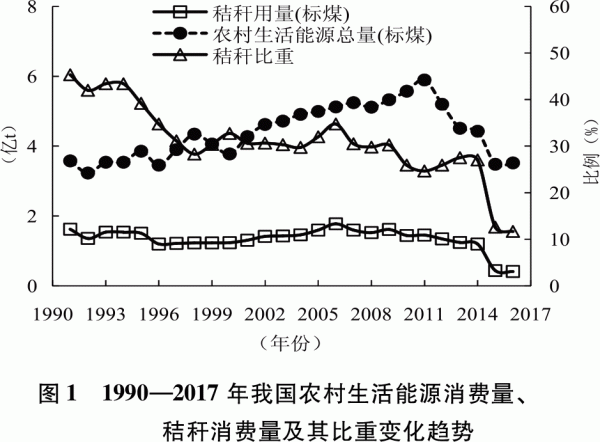
2.3秸秆资源量的变化
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农作物产量的“十三连丰”,秸秆的产生量也随之增加。1991年我国秸秆产生量约6.24亿t[9],截止“十二五”末,秸秆资源总量达到10亿t左右[2],年均增幅约2.7%,日益增长的秸秆量亟需找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出路和解决途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一步造成秸秆产生量的多变性。王亚静等[10]研究表明,以“镰刀弯”地区玉米调减为主要内容的种植业结构调整较2015年可减少玉米秸秆产出1501万t。与此同时,随着东北寒地井灌稻和南方双季稻产区釉稻调减、“粮改饲”试点和休耕轮作试点的同步推进,区域秸秆资源总量、种类和供需平衡状态将发生重要变化,对现有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布局带来更加严峻挑战(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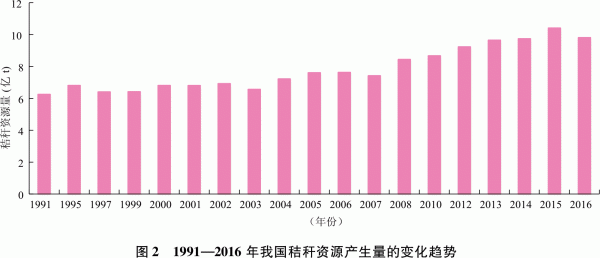
2.4农作物茬口季节矛盾
前茬作物收获与下茬作物适期播种之间的时间短促,严重影响秸秆在田间晾晒和收集,季节矛盾紧张是秸秆处置所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造成秸秆焚烧和废弃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江苏省北部为例,主要作物轮作方式为水稻一小麦和玉米一小麦轮作。在稻麦轮作条件下,中熟中梗水精品种全生育期已延长至150-155d,半冬性小麦品种最佳播期为10月中旬,全生育期230~240d。由于当地水稻种植方式的重大改变(直播都和机插秧),使秧龄期大幅缩短(0-20d,较人工插秧少10-30d),导致水稻收获期大幅延迟,明显错过小麦播种适期,而晚播小麦的成熟期也相应推迟,导致小麦收获期与水租适栽(播)期重叠,稻麦轮作步入水稻收割晚一小麦播期迟一小麦成熟晚一水程载描(种植)迟的循环[6]。加上稻麦收获李节降雨等气象因素,使秸秆在田间缺乏有效的处理时间[11],对秸秆需求企业来说难以保证秸秆原料的有效供应(表1)。

3秸秆综合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秸秆还田的问题
秸秆机械化粉碎直接还田是目前解决秸秆焚能问题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当前在結秆机械还田的农机和农艺枝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就秸秆“如何还下去、如何还得好”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农作物收获留茬过高,秸秆机械还田困难,其直接原因是机械收获陈本,以小麦秸秆为例,留茬高度从20cm降低到10cm时,收割机械工作效率下降18.7%-39.9%,油耗增加4.6%-4.7%,收割成本增加10.1-24.6元/667㎡[12]中。二是还田作业成本高。以东北地区为例,要达到理想的还田效果,需经过作物收货、秸秆粉碎抛洒、旋耕破茬、撒施腐熟剂、机械翻耕、圆盘耙耙平等多道工序,每667㎡作业或本增组100元左右[13];李建政[14]对黄淮海地区玉米秸秆还田的研究也显示,不同还田方式作业成本增加了76-88/667㎡。三是配套农艺措施不完善。要达到良好的作业水平,需要对秸秆进行2次以上的粉(切)碎和旋耕,而且要与深松和定期深翻相结合。但实际生产中多数田地只能做到粉碎和旋标1次,且后续水、肥、植保、全苗壮苗等救增技术不配套,极大影响了后茬农作物播种和正常生长。四是缺乏区域秸秆还田适宜性的研究,技术规范不明确。由于各地在土壤类型、质地及气象条件、农作制度、地形地貌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秸秆还田量、还田时序、还田方法、还田时期等方面缺乏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在秸秆还田技术推广应用中难免产生一些负效应,普遍存在着秸秆还多少,还多久、怎么还等问题[15],实际操作中凭感觉、靠经验的现象比较普遍。五是机具设备的不配套。国产大马力拖拉机、秸秆抛撒、深翻等专用配套设备普遍缺乏,无法实绝秸秆深翻还田和高效作业,同时缺乏丘区,山区秸秆快速还田相关配套机具和设备。
3.2产业化发展何题
目前,秸秆综合利用的各种途径产业化发展缓慢,产业链短或者缺失,单一效益低,辐射带动作用不强。一方面秸秆产品受“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秸秆资源化利用成本较高,涉及机械成本、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储存成本,加工成本等,而秸秆产品价格与其相应替代的高品价格比较不具优势,产业化发展困难[16]。另一方面秸秆综合利用研究基础尚待加强、系统性、规模化和集成化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尚待突破[17]。在肥料化利用方面,秸秆生物腐熟技术效率低,腐熟过程中还存在养分丢失问题。在饲料化利用方面,秸秆青贮防霉、氨化技术需要与饲养管理,词料搭配、畜种改良和疫病防控等技术进一步配套组合;秸秆揉搓、菌剂添加、包膜等一体化饲用收获设备供给能力产重不足。在燃料化利用方面,秸秆气化中的焦油处理、秸秆乙醇产业化生产效益不高等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尚未完全突破;秸秆固化、碳化生产设备产量低,能耗高,寿命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原料化利用方面,秸秆复合材料、生产板材和清洁制浆等生产工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良。在基料化利用方面,秸秆育秧基质、育苗基料、动物垫床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突破还不够。以我国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出台的秸秆利用相关标准为例,除秸秆发电厂、秸秆板材、秸秆招气外,相关行业标准多涉及机被作业质量,缺乏秸秆产品生产技术规流,与现实利用拉术而接不够,降低了秸秆利用技术实际应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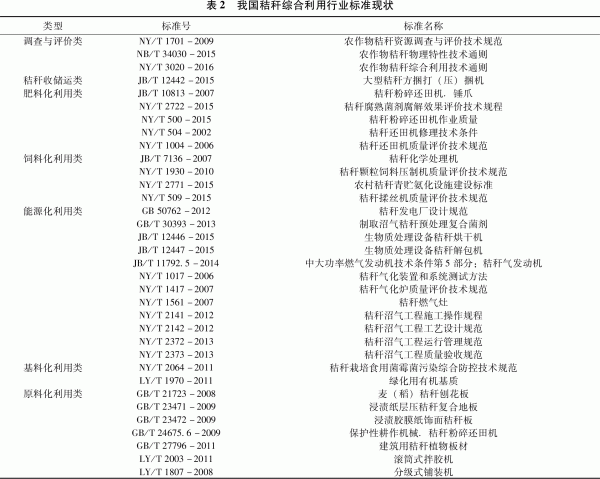
3.3收储运体系问题
秸秆收集难,运输难,储存难等问题在大部分区域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收储运体系不完善越来越成为制约秸秆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是收铺成本高。徐亚云等[18]对华北平原不同秸秆收储运模式(分为集中型、分散型;人工收集、机核收集等)的研究表明,秸秆收储运成本一般在120-260元/t之间,秸秆收储运能耗在(1.2-5.5)×105kJ/t之间;田间机械收集比人工捡拾成本低,但所需设备投资和能耗较高;二是收储运装备水平低。国内现有设备产品普遍存在实用性和可靠性较差的问题,缺乏适合不同地形的高效秸秆收集打包机械,同时机械价格较高、一次性投资大、季节性强、作业时间短,影响农民购机从事秸秆收集的积极性;三是秸秆存储用地矛后日益突出。土地租金高或土地指标缺等因素造成收储点建设困难,目前国家层面鼓励秸秆收储用地按临时用地管理,仅少部分省份将其纳入农用地管理范畴。四是秸秆运输半径受或本限制。王雪等[19]研究表明平均每吨秸秆的运输费用为2.29元/km,不适于长距离运输;其他针对秸秆发电厂的研究也提出秸秆的运输手径小于50kamm会获得最佳经济效益[20]。
3.4激励政策问题
一方面关键性政策工具尚未破题。现有秸秆资源化利用政策以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农机购置补贴和发电上网价格补贴为主,但在秸秆还田补贴、秸秆储存用地,秸秆运输绿色通道、秸秆初加工用电和终端产品应用等关接开节最乏相应的教知收笙,不和于形或完整的产业位,另一方面结行锄合利用是一项对会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迫切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但目前的财政补贴存在补贴作物种类有限、补贴金额有限、补贴区域有限、补贴对象重点不明确等问题[16],且现有的资金投入渠道大多以项目的形式集中在耕地质量提升、试点建设等方面,缺乏普惠性、针对性的资金扶持,难以实现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推动。以秸杆还田为例,通过粉碎、翻耕、旋耕等标准化作业后,其机械作业成本大大增加,目前只有江苏省对苏南、苏中、苏北分别实行为10、20、25元/667㎡的普惠性补贴[21],其余各地的还田补贴大多局限于一些重点地区或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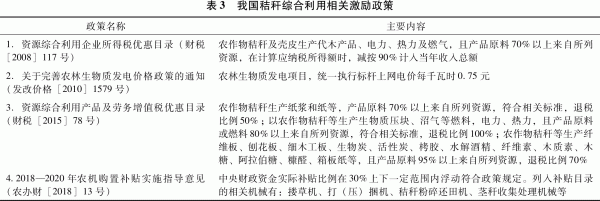
4秸秆综合利用对策建议
4.1推进县域秸秆全量利用
我国秸秆量大、面广,必须走“区域统筹、整体推进”的全量化利用路径,才能破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难题,最大规模地实现桔杆资源化利用[22]。各地应遵循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以县域为单元,按照“估算秸秆资源与可收集量、调研秸秆综合利用现状、确定维持地力的秸秆还田量、设计秸秆离田利用的比例关系、合理布局秸秆产业和收储场地、健全秸秆全量处理利用的政策保障体系”[23]等基本设计思路编制秸秆全量化利用实施方案,在县域范围内因地制宜地推广“秸秆农用十大模式”[24],优化“五料化”利用产业布局。
4.2分区施策确定秸秆利用方向
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作物品种、种养业结构、地理气候、生产生活用能等,因地制宜确定秸秆综合利用的主攻方向。总体来看,东北玉米单作区应以秸秆还田为主,能源燃料化和饲料化为辅;西北农区应以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同步推进为主;黄淮海玉米一小麦轮作区、长江中下游水稻(油菜)一小麦轮作区以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以饲料化利用为辅;华南水稻一水稻轮作区农区则主推秸秆还田利用[2]。各地区的秸秆还田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东北玉米单作区可重点推广秸秆粉碎深翻还田技术,即玉米机收、秸秆粉碎(10cm以内)一机撒腐熟剂、氮肥一大马力深翻(2-3年一次,耕层30cm以上)一旋耕整地。黄淮海玉米一小麦轮作区的小麦秸秆采取机收粉碎一高留茬一免耕玉米播种的技术流程,玉米秸秆还田可采取籽粒机收、秸秆粉碎(10cm以内)一机撒腐熟剂、氮肥一深翻(3年一次,耕层25cm以上)一旋耕整地的技术流程。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的水稻秸秆适宜采取稻谷机收,秸秆切碎匀抛一秸秆日晒1~2d(秸秆含水率低时可忽略)一甩刀式秸秆粉碎机粉碎一旋耕(耕层15cm以上)一施肥一下茬作物种植的技术流程[24]。
4.3加强政策工具创设
将秸秆综合利用政策纳入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框架内,不断引导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优化集成和创设配套[1]。在秸秆还田方面,建议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对实施秸秆还田的成本增量按照60%予以补贴;同时对秸秆还田所需的大马力拖拉机、高质量秸秆粉碎机、腐熟剂喷洒设备等进一步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标准,实行不限量敞开补贴。在秸秆离田利用方面,建议各地将秸秆收储点和堆场等用地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落实秸秆初加工享受农业用电价格政策,并逐步扩大到秸秆转化利用全链条给予一定的用电价格优惠;参照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的做法,享受运输费用减免政策;推动秸秆收储,加工企业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并真正纳入绿色信贷统计制度。
4.4扩大试点示范引导
建议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投人,把农财两部实施的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和粮棉主产区。在试点区城、以县为单元因地制宜确定秸秆综合利用的结构和方式,探索秸秆还田、秸秆离田和终端产品应用的补贴标准,培育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形成工作措施、技术措施、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整县推进秸秆利用模式,健全政府、企业与农民三者利益统一的联结机制,不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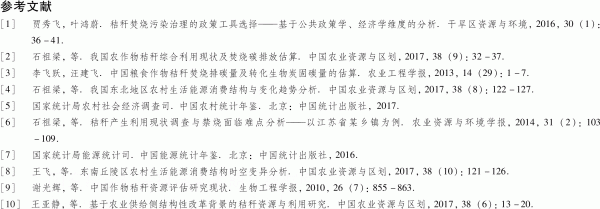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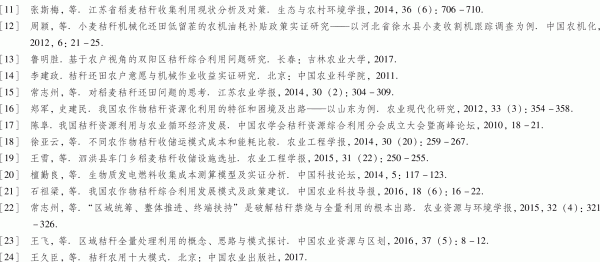 |

